在 Watch of the Week 中,我們邀請了 HODINKEE 的員工和朋友來解釋他們?yōu)槭裁聪矚g某件作品。本周的專欄作家是Esquire 、 Town & Country和Men’s Vogue的前主編 。
“對不起,”大約 35 年前,一個人對我說。“你碰巧有時間嗎?”
這是一個足夠合理的問題。我戴著手表。雖然它不是我夢寐以求的那些,貴族藝術(shù)裝飾勞力士王子或我在拉爾夫勞倫廣告中看到的復(fù)古卡地亞坦克,但它很相似 – 矩形形狀和彎曲以包裹手腕,再加上這個其中一個有折線形亞克力水晶,讓我想起了我也想要的 Split-Window 356 Porsche。

我找到了這塊手表,它是 1930 年代的 Benrus,經(jīng)過大量搜尋,我去了三個不同的跳蚤市場。然后我在圣安東尼奧的 Polo Shop 花了兩倍的錢買了一條新的琥珀色蜥蜴皮表帶,我在那里有一份高中工作。這是學(xué)習(xí)如何成為風(fēng)格清道夫、如何讓事情發(fā)揮作用的開始。只有一個問題:它沒有。手凍僵了,我花了大約 30 美元按原樣買了它。
“嗯,”我對陌生人說,表現(xiàn)得好像真的相信通過查看我手腕上的道具就能找到他問題的答案。“我好像忘記給手表上弦了。”
恐怕這種事發(fā)生過不止一次。最終,我的一些裸手朋友多次收到該回復(fù),開始取笑我這種虛構(gòu)的行為。但我在乎什么?我在追逐超越時間的東西。
并不是我不想讓我的手表工作。是我送它去修理的手表店告訴我它不值得修理;我最好找一個新的。
不久之后,一個慷慨的女朋友解決了我的問題,在 1989 年我生日那天,她給了我另一只 Benrus,這是一款 1950 年代的正裝手表,帶有 Cornes de Vache 表耳和溫文爾雅的黑色表盤。當(dāng)我纏繞它時,這個真的滴答作響。我把我的好帶子戴上了,那只壞了的表被放進了一個黑暗的抽屜的后面。

我忠實地佩戴了新的好幾年,即使在我們分手之后,直到我大學(xué)畢業(yè)并搬到紐約后,我終于買到了我的第一塊勞力士——一只 1971 年的 Oysterdate,它的外觀非常接近 1930 年代的 Bubblebacks我一直想要,只是它沒有引擎蓋凸耳。它就在我每天路過的市中心一家當(dāng)鋪的櫥窗里,明白了,我用這個品牌送給我的 Donna Karan 天文鐘進行了交易,進行了等額交換。對不起,唐娜,但這一刻,恐怕,已經(jīng)注定了。
從那時起,我越來越有辦法在跳蚤市場以外的地方購物,我找到了擁有其他勞力士手表的方法,而且,在一個非常幸運的日子,我買了一只江詩丹頓 American 1921,在這個通貨膨脹的時代,我把一大瓶 1990 年柏圖斯 (Petrus) 酒放在銀行保險箱里,作為財富的儲藏室。然而,前幾天為了不同的寫作任務(wù)重讀了不起的蓋茨比,我開始思考 1920 年代的過渡品味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如何必然地發(fā)明手表的,因此戰(zhàn)壕中的士兵可以同步軍隊的行動在戰(zhàn)斗中——散發(fā)出異常優(yōu)雅的美感。
戰(zhàn)爭扼殺了新藝術(shù)運動,正如羅伯特·休斯 (Robert Hughes) 曾經(jīng)說過的那樣,“在手工和其作品被機器產(chǎn)品淹沒之前,對工藝敏感性的最后一次精致抗議”。但它對奢侈材料、精致線條和裝飾性裝飾的信念融入了裝飾藝術(shù)的取而代之的東西中。作為一種運動,它給了我們克萊斯勒大廈、最好的點煙器、最令人難忘的歐洲開胃酒海報,以及各種傳奇汽車最具標志性的引擎蓋裝飾,僅舉幾例。它還塑造了手表設(shè)計的早期幾十年,包括所有最先引起我注意的設(shè)計。

這引起了我的思考。是的,American 1921 是那個(或任何)時代手表崇高的最高典范之一,但為什么,我的許多夢想都被 Bubblebacks 和雙表盤勞力士醫(yī)生手表的幻象所打擾,尤其是 Jump Hour,難道我沒有看過各種圣杯手表的炒作,看到這些被大大低估的寶石的例子嗎?而且,更糟糕的是,為什么我背棄了我值得信賴的老朋友本魯斯,他是幫助我成為一個不再總是遲到的人的工具,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仍然知之甚少?
我隱約知道 Benrus 是一家美國公司,它進口瑞士零件來制造手表。這個名字是創(chuàng)始人名字 – Benjamin Lazarus 的合成詞,他于 1921 年與他的兩個兄弟在曼哈頓中城的 Hippodrome 大樓開設(shè)了商店。它作為一個價格合理的理想品牌進行營銷,這是一種質(zhì)量上乘、設(shè)計精良的產(chǎn)品,通過名人代言的早期實踐者:本魯斯為查爾斯·林德伯格創(chuàng)作了《飛俠》;Babe Ruth 的運動手表;并且,在 1963 年,JFK 在他的收藏中增加了一個。也許該品牌最有趣的營銷妙招純屬偶然。廣告
在Bullitt的拍攝期間,Steve McQueen 決定佩戴民用版的 Benrus DTU 2A,這是一款軍用規(guī)格的越南主力腕表,其簡單的表殼和干凈的表盤讓人回想起戰(zhàn)壕表的實用優(yōu)雅。包括 Benrus 的檔案保管員 Darius Solomon 在內(nèi)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為什么與他的 Monaco Heuer 和 Rolex Submariner 關(guān)系最密切的 McQueen 選擇了這款特別的手表。“當(dāng)時的想法是,這是他的,他只是決定戴上它,”所羅門說。Arthur Barens 是 McQueen 多年的律師,現(xiàn)在代表他的遺產(chǎn),他說他并不感到驚訝。“史蒂夫經(jīng)常喜歡在他的電影中穿非品牌的東西。”

對于那些碰巧知道這個關(guān)于麥昆傳奇人物的略微外圍故事的人來說,他的 DTU #3061 被稱為 Benrus “Bullitt”。與現(xiàn)場版本不同,它有一個拋光的而不是帕克化的表殼,秒針尖端有一個紅色箭頭。Benrus 根據(jù)合同為美國軍方制造的 DTU 2A 本月早些時候重新發(fā)布。它的聲譽和稀有性正在推動一個好的復(fù)古例子的價格高于你的預(yù)期,特別是如果它有一個顯著的歷史。
2019 年在 Phillips Game Changers 上拍賣了兩塊 Benrus 軍用手表——一塊 1968 年的 DTU 和一塊大約 1965 年的 Ultra Deep,這是一款潛水表,其扁平表殼具有氣泡背的氛圍。曾在老撾服役的一名空軍軍士長曾佩戴過這些手表,后者是一位將心理戰(zhàn)進行到野蠻程度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安東尼·波謝普尼;他指示在他手下服務(wù)的人切斷殺戮的耳朵,人們普遍認為這是馬龍白蘭度在現(xiàn)代啟示錄中賦予庫爾茨角色的更新旋轉(zhuǎn)的靈感。木槌價格為 30,000 美元。
由于我對 Benrus 的潛在教育,我現(xiàn)在和以往一樣是該品牌的粉絲。DTU、Ultra Deep 和另一個名為 Sky Chief 的美女都成為我擁有的手表中的前列。事實上,我看到你可以在最大的跳蚤市場 eBay 上買到看起來非常漂亮的任何這些模型的版本,而不是那么多。特別是如果您不介意擁有一個下次陌生人問您時間時可能無法使用的東西。
原創(chuàng)文章,作者:LNG復(fù)刻,如若轉(zhuǎn)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mohanpet.cn/1861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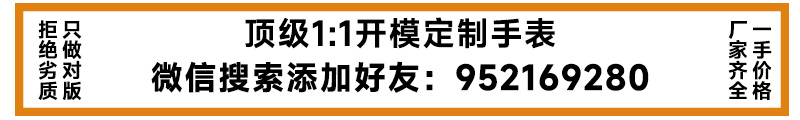
 微信掃一掃加客服
微信掃一掃加客服 

